
- 长河血(齐修远陈志远)最新小说全文阅读_最新章节列表长河血(齐修远陈志远)
- 分类: 言情小说
- 作者:南派的神
- 更新:2025-04-27 18:29:41
阅读全本
古代言情《长河血》,由网络作家“南派的神”所著,男女主角分别是齐修远陈志远,纯净无弹窗版故事内容,跟随小编一起来阅读吧!详情介绍:1900年,八国联军铁蹄踏破北京城,名医齐修远在战火中救下孤儿陈志远,目睹清廷腐朽,萌生救国之心。辛亥风云,军阀混战,抗日烽火……陈志远从军报国,齐修远以医济世,两人与革命青年林书瑶在时代洪流中相遇。从戊戌变法到新中国成立,五十年家国沧桑,三代人前赴后继,用热血与信念铸就一部荡气回肠的保家卫国史诗。
他睁开眼,发现右手食指上扎着根细小的银针——昨夜太累,竟趴在药案上睡着了,手里还攥着给陈志远施针用的毫针。
窗外,知了声嘶力竭地鸣叫着,仿佛要把盛夏最后的热度都喊出来。
"先生..."陈志远光着脚站在药柜旁,手里捧着个缺口的青瓷碗,"我熬了粥。
"齐修远拔掉指上的银针,看着孩子左腿上的绷带——那里己经不再渗血,但走路时还是会不自觉地跛一下。
六天前从瓦砾堆里救出的小乞丐,如今穿着改小的夏布衫,乱蓬蓬的头发也束成了规整的总角,只是眼睛里还藏着惊弓之鸟般的警惕。
"德海呢?
"齐修远接过碗,米粥稀得能照见人影,底下沉着几片野菜。
"去前门大街换药了。
"陈志远踮脚去够药柜顶层的陶罐,露出腰间一片淤青——昨天被英国兵推搡时撞的。
"冯大人说今天要带军医来看诊室。
"齐修远的手顿了一下。
自从三天前救治了那个德国少校,冯·克莱斯特中尉就频频造访,有时带些奎宁粉之类的稀罕药品,更多时候是来借医书。
这个左颊带疤的德国军官总爱用马鞭敲打皮靴,眼睛却总往地窖方向瞟。
"把《伤寒杂病论》收起来。
"齐修远三口喝完粥,起身拉开药柜暗格,"还有你爹给你的长命锁,都藏到西厢房夹壁里。
"陈志远点点头,突然竖起手指:"马蹄声!
"果然,街口传来嘚嘚的马蹄声,夹杂着德语吆喝。
齐修远迅速系好长衫纽襻,顺手把案上的《海国图志》塞进袖中。
大门被推开时,阳光在地上投下三个长长的影子——冯·克莱斯特带着两个军医站在门口,马刺上的血渍还没擦干净。
"齐医生,"德国人用生硬的中文说道,"这位是穆勒上尉,汉堡大学医学博士。
"高个子军医摘下白手套,伸出手:"您救治施密特少校的手法令人印象深刻。
"齐修远注意到对方指甲缝里残留着血迹,袖口却别着枚精致的蛇杖徽章——那是欧洲医学生的毕业标志。
他微微颔首:"简陋医术,不值一提。
""听说您在海德堡学习过?
"穆勒上尉蓝眼睛里闪着兴趣,"我们正在组建临时医院,需要本地医生协助。
"冯·克莱斯特的马鞭突然指向陈志远:"这孩子会英语?
""家父曾在海关任职。
"齐修远不动声色地把孩子往身后挡了挡。
陈志远却探出头,用英语流利地说:"先生们需要茶还是咖啡?
"两个德国军官惊讶地对视一眼。
穆勒上尉蹲下身,从口袋里摸出块巧克力:"聪明的孩子。
你叫什么名字?
""陈志远。
"孩子接过巧克力却没吃,而是塞进袖袋,"意思是志向远大。
"德国人走后,医馆重归寂静。
齐修远翻开穆勒留下的德文医学手册,铜版纸上印着最新式的外科器械图样。
陈志远趴在一旁临字帖,毛笔尖在"仁心仁术"西个字上反复描画。
"先生,"孩子突然问,"德国人为什么杀我们的人,又要我们帮忙?
"毛笔在"术"字的最后一捺上洇开墨团。
齐修远望着窗外被炮火削去半边的槐树,想起海德堡医学院图书馆里那些安静读书的德国同学。
"人病了要吃药,"他慢慢说,"国家病了,就会发疯。
"未时二刻,张德海跌跌撞撞跑回来,脸色煞白:"先生!
菜市口...在杀头!
"齐修远正在研磨犀角,闻言石杵砸在臼里,溅起几点药末。
他抓起药箱就往外走,陈志远像条小尾巴似的紧跟在后。
长庆街比往日更萧条,几家店铺门板上贴着联军告示,墨迹未干的德文与中文并列:"窝藏拳匪者,格杀勿论。
"菜市口刑场围满了人。
齐修远挤到前排时,正看见刽子手举起鬼头刀——那是个穿着英军制服的印度兵,包头巾下渗出汗水。
跪着的犯人突然仰头喊了句什么,刀光闪过,头颅滚到齐修远脚边,眼睛还睁着,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。
"说是义和团余党。
"旁边卖炊饼的老汉低声道,"其实就是个掏粪的,捡了面红旗当抹布..."陈志远死死攥住齐修远的衣角,指甲隔着布料掐进肉里。
齐修远弯腰想捂住孩子的眼睛,却听见一声微弱的呻吟——刑场角落的排水沟里,躺着个血肉模糊的人影。
"还活着!
"齐修远冲过去,发现是个瘦小的中年人,右肩被子弹贯穿,腰间挂着个摔碎的砚台。
他迅速按压伤口止血,那人却挣扎着凑到他耳边:"南...南方...孙...""别说话。
"齐修远撕下衣摆包扎,血立刻浸透布料。
身后传来英军士兵的呵斥,他头也不回地用英语喊道:"这个人是我的药童!
"回医馆的路上,张德海背着伤者,不时左顾右盼。
陈志远小跑着跟在后面,怀里紧紧抱着齐修远的药箱。
转过观音寺胡同,突然闪出三个日本兵,明晃晃的刺刀横在路中央。
"站住!
"领头的军曹一把扯开伤者衣襟,"枪伤!
反抗军!
"齐修远深吸一口气,从袖中掏出冯·克莱斯特给的通行证。
日本军曹狐疑地翻看证件,突然用生硬的中文问:"你会接骨吗?
"原来日军驻地有个少尉坠马摔断了腿。
齐修远给伤者灌下麻沸散,在陈志远协助下完成接骨时,夕阳己经西斜。
日本军医送他们出来时,悄悄塞给齐修远一小包磺胺粉。
"南方..."担架上的神秘伤者当晚发起高烧,不停呓语着"起义""电报"之类的词。
齐修远用银针刺他人中穴,才发现他舌下藏着片薄如蝉翼的纸条,上面用蝇头小楷写着"八月十五,武昌"。
七月初八凌晨,伤者死了。
齐修远在整理遗物时,从对方鞋垫里找出张被血浸透的地图,上面标着几条奇怪的运输路线。
他把尸体埋在后院梨树下,陈志远蹲在一旁默默递工具,突然问:"先生,武昌在哪?
""长江边上。
"齐修远铲起一抔土,"很远。
""比海德堡还远吗?
"齐修远的手顿了顿。
十年前乘船离开汉堡港时,他以为那将是此生去过最远的地方。
如今站在满目疮痍的北京城里,却觉得欧洲近在咫尺,而武昌——那个从未去过的城市,反倒远得像在天边。
"先生看!
"陈志远突然指着天空。
一群信鸽掠过灰蒙蒙的晨雾,脚环在朝阳下闪着金光。
齐修远认出那是庆王府养的鸽子,往日这时候该往西飞,今天却齐齐转向东南。
七月初十,冯·克莱斯特带来个惊人消息:德军司令部批准齐修远重开医馆,专门救治联军中的热病患者。
德国人留下两箱药品和十袋面粉,还有本崭新的德汉词典。
"穆勒上尉很欣赏你。
"德国军官用马鞭轻敲靴筒,"下个月德皇特使来访,需要展示文明治理成果。
"齐修远抚摸着词典烫金的封面,想起海德堡旧书店里那个总给他留座的老店主。
"我需要通行证,"他说,"药材不够了。
""每天酉时前必须回来。
"冯·克莱斯特眯起眼睛,"听说昨天日本兵在你们后院挖出具尸体?
"陈志远正在擦拭显微镜,闻言手一抖,目镜滚到地上。
德国军官弯腰捡起来,突然用德语问:"孩子,你见过电报机吗?
""只在外滩海关见过一次。
"陈志远不假思索地用英语回答,又立刻改口德语,"是父亲带我去看的。
"冯·克莱斯特意味深长地看了齐修远一眼,临走时故意落下个牛皮公文包。
齐修远打开一看,里面是份标注着联军布防情况的地图,还有张照片——一队德国兵站在堆成小山的头颅前咧嘴笑着。
"收好。
"齐修远把地图塞给陈志远,"夹在《本草纲目》扉页里。
"七月十二,齐修远带着陈志远去城南搜罗药材。
被炮火轰塌的仁济堂药铺里,他们扒出半罐发霉的龙眼肉和几包虫蛀的当归。
回来的路上经过英国兵把守的粮仓,看见几十个百姓排队领救济粥,有个瘦成骨架的老妇人突然栽倒,再没起来。
"是霍乱。
"齐修远拦住要上前查看的陈志远,"去药铺后头找些苍术来,越多越好。
"当天夜里,齐修远熬了三大锅避瘟汤,让张德海分给街坊。
陈志远蹲在灶前添柴,小脸被火光映得通红。
他突然说:"先生,我想学把脉。
"齐修远搅动药汤的手停住了。
十年前父亲也是这样在瘟疫流行时连夜熬药,而他蹲在同一个位置,说出同样的话。
药气氤氲中,他仿佛看见父亲花白的辫子在蒸汽里晃动。
"手伸过来。
"齐修远擦干手,把孩子的三根手指按在自己腕上,"静心,数呼吸。
"陈志远屏息凝神的样子像个缩小版的郎中。
齐修远看着他睫毛在火光中投下的阴影,想起那个死在梨树下的陌生人。
武昌要发生什么?
那张地图又意味着什么?
七月十五中元节,本该烧纸祭祖的日子,京城却静得像座坟。
齐修远在后院摆了张矮几,供上三个馒头——给父亲,给死在刑场的无名氏,也给陈志远从未谋面的父母。
陈志远学着他的样子焚香叩拜,突然问:"人死了真的会变成鬼吗?
""会变成星星。
"齐修远指着刚亮起的天狼星,"你爹娘就在那看着你。
"孩子仰头望着星空,眼泪无声地流到腮边。
齐修远轻轻揽住他单薄的肩膀,感觉掌心下的骨头硌得生疼。
夜风掠过梨树,那片新翻的土己经长出嫩草。
七月十八,穆勒上尉突然造访,带来个发着高烧的法国军官。
齐修远诊脉后发现是伤寒,用白虎汤加减治疗。
德国军医全程观摩,对齐修远在病人脚底敷吴茱萸的手法大为惊叹。
"太神奇了!
"穆勒捧着笔记本狂记,"这比我们用的冰敷法有效多了!
"齐修远正在写药方,闻言笔尖一顿。
他想起海德堡教授说过的话:"医学不该有东西之分,只有有效与无效之别。
"陈志远机灵地递上刚烘干的药碾,里头是捣好的羚羊角粉。
"先生,"送走德国人后,陈志远小声问,"洋人为什么总说我们落后,又要学我们的医术?
"齐修远正在擦拭被法国人弄脏的诊榻,闻言首起腰来。
透过支摘窗,可以看见德国兵在对面屋顶架设电报天线,细长的金属线在夕阳下闪着冷光。
"知道针灸为什么能止痛吗?
"他反问道。
陈志远摇摇头。
"因为人体自有经络,与种族无关。
"齐修远指着院里的梨树,"就像这棵树,德国人叫它birne,英国人叫pear,可结的果子都一样甜。
"七月二十,冯·克莱斯特突然派兵"请"齐修远去给日本领事看病。
回来时己是深夜,陈志远还守在灯下抄《汤头歌诀》,见他进门立刻端来热在灶上的杂粮饭。
"日本领事得了怪病,浑身起红疹。
"齐修远疲惫地坐下,从袖中摸出个小纸包,"这是他们军医用的消炎片,收好。
"陈志远好奇地拆开纸包,里面是两片白色药片和一张字条。
他展开一看,上面用德文写着:"八月一日,待在医馆。
""先生..."孩子刚开口,就被齐修远制止。
院墙外传来巡逻兵的皮靴声,由近及远,最终消失在夜色中。
"明天开始,"齐修远吹灭油灯,在黑暗中小声说,"我教你认德文字母。
"七月二十二,酷暑难当。
齐修远带着陈志远去什刹海采芦苇根,看见湖面漂着几具肿胀的尸体,有野狗在岸边啃食。
他们绕道西西牌楼,发现贴满联军告示的墙下多了张新布告——朝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,即将与联军议和。
"先生,议和是什么意思?
"陈志远踮脚看着布告。
"就是..."齐修远突然哽住。
十年前他离开德国时,柏林报纸上登着胶州湾事件的照片,标题是《德国在亚洲的又一胜利》。
如今站在残破的牌楼下,他忽然明白了一个残酷的事实:弱国的书生,连解释"议和"二字的资格都没有。
回家路上经过英国兵营,听见里面传出留声机的音乐声。
陈志远扒着门缝偷看,被齐修远拽回来时小声说:"他们在跳舞...还有个穿红裙子的中国女人..."齐修远捂住孩子的嘴快步离开。
转过两条胡同,迎面撞见张德海慌慌张张跑来:"先生!
快回去!
德国兵把医馆围了!
"医馆门口站着六个持枪德军,冯·克莱斯特正在翻检药柜。
见齐修远回来,他啪地合上手中的《瘟疫论》:"有人举报你藏匿革命党。
""这里只有医生和病人。
"齐修远平静地说,感觉陈志远的手在他掌心发抖。
德国军官冷笑一声,突然用马鞭挑起地窖盖:"是吗?
那下面是什么?
"地窖里躺着三个霍乱患者,都是附近街坊。
齐修远刚要解释,穆勒上尉匆匆赶来,在冯·克莱斯特耳边低语几句。
德国军官脸色变了又变,最终只是狠狠踢翻了药碾。
"明天起,所有病人必须登记。
"他甩下一叠表格,"包括死亡证明。
"当晚,齐修远在灯下研究那张神秘字条。
陈志远己经熟睡,手里还攥着德语单词本。
窗外月光如水,照得梨树下那片新草格外青翠。
远处隐约有马蹄声,像是从东交民巷方向传来的。
七月二十五,暴雨。
齐修远正在教陈志远配药,大门突然被撞开。
一个浑身湿透的清军军官跌进来,右胸插着半截箭矢。
张德海刚要关门,街口传来日本兵的哨声。
"求您..."军官咳着血沫,"把...这个...交给..."他塞给齐修远个油纸包,就断了气。
暴雨掩盖了血迹。
齐修远把尸体藏进地窖,打开油纸包——里面是把精致的左轮手枪,枪柄上刻着"楚"字。
陈志远瞪大眼睛,小手不自觉地摸向枪管。
"去烧锅开水。
"齐修远迅速包好枪,塞进灶台暗格,"再把《伤寒论》拿来。
"雨声渐歇时,日本兵来搜查"逃兵"。
齐修远用流利的日语解释死者是霍乱患者,还故意让他们看溃烂的伤口。
军曹捂着鼻子退出去,在门槛上绊了个趔趄。
七月二十八,齐修远被紧急召去德国公使馆。
回来时带了个沉重的皮箱,里面装满医学书籍和手术器械。
陈志远发现先生的白布袜上沾着血迹,袖口也少了一颗盘扣。
"公使夫人难产。
"齐修远轻描淡写地说,从怀里摸出个苹果给孩子,"穆勒上尉送你的。
"陈志远啃着苹果看齐修远整理书籍,突然指着本德文书惊呼:"先生!
这上面有枪!
"那是一本《战地急救手册》,扉页照片里排列着各式武器。
齐修远快速翻到某页,指着一行德文念道:"止血带使用不宜超过两小时——这才是重点。
"夜深人静时,齐修远悄悄取出油纸包。
手枪在月光下泛着蓝光,枪膛里还有三发子弹。
他想起白天在公使馆听见的只言片语——俄国人增兵东北,德国准备强租胶州湾,而南方某个港口城市,似乎爆发了起义。
七月三十,陈志远第一次完整写下自己名字。
毛笔在宣纸上划出稚拙的笔画,最后一捺却力透纸背。
齐修远看着这个从废墟里捡来的孩子,忽然想起《庄子》里的话:"泉涸,鱼相与处于陆,相呴以湿,相濡以沫...""先生,"孩子举着字纸,眼睛亮晶晶的,"我写得对吗?
"齐修远摸摸他刚长出发茬的头顶:"很好。
明天教你写天下为公。
"窗外,暮色中的北京城炊烟袅袅。
不知谁家在烧艾草,苦涩的烟味飘进医馆,与药香混在一起。
更远处,联军军营的探照灯划破夜空,像柄雪亮的长剑,刺向东南方的星辰。
《长河血(齐修远陈志远)最新小说全文阅读_最新章节列表长河血(齐修远陈志远)》精彩片段
庚子年七月初六,天刚蒙蒙亮,齐修远就被一阵刺痛惊醒。他睁开眼,发现右手食指上扎着根细小的银针——昨夜太累,竟趴在药案上睡着了,手里还攥着给陈志远施针用的毫针。
窗外,知了声嘶力竭地鸣叫着,仿佛要把盛夏最后的热度都喊出来。
"先生..."陈志远光着脚站在药柜旁,手里捧着个缺口的青瓷碗,"我熬了粥。
"齐修远拔掉指上的银针,看着孩子左腿上的绷带——那里己经不再渗血,但走路时还是会不自觉地跛一下。
六天前从瓦砾堆里救出的小乞丐,如今穿着改小的夏布衫,乱蓬蓬的头发也束成了规整的总角,只是眼睛里还藏着惊弓之鸟般的警惕。
"德海呢?
"齐修远接过碗,米粥稀得能照见人影,底下沉着几片野菜。
"去前门大街换药了。
"陈志远踮脚去够药柜顶层的陶罐,露出腰间一片淤青——昨天被英国兵推搡时撞的。
"冯大人说今天要带军医来看诊室。
"齐修远的手顿了一下。
自从三天前救治了那个德国少校,冯·克莱斯特中尉就频频造访,有时带些奎宁粉之类的稀罕药品,更多时候是来借医书。
这个左颊带疤的德国军官总爱用马鞭敲打皮靴,眼睛却总往地窖方向瞟。
"把《伤寒杂病论》收起来。
"齐修远三口喝完粥,起身拉开药柜暗格,"还有你爹给你的长命锁,都藏到西厢房夹壁里。
"陈志远点点头,突然竖起手指:"马蹄声!
"果然,街口传来嘚嘚的马蹄声,夹杂着德语吆喝。
齐修远迅速系好长衫纽襻,顺手把案上的《海国图志》塞进袖中。
大门被推开时,阳光在地上投下三个长长的影子——冯·克莱斯特带着两个军医站在门口,马刺上的血渍还没擦干净。
"齐医生,"德国人用生硬的中文说道,"这位是穆勒上尉,汉堡大学医学博士。
"高个子军医摘下白手套,伸出手:"您救治施密特少校的手法令人印象深刻。
"齐修远注意到对方指甲缝里残留着血迹,袖口却别着枚精致的蛇杖徽章——那是欧洲医学生的毕业标志。
他微微颔首:"简陋医术,不值一提。
""听说您在海德堡学习过?
"穆勒上尉蓝眼睛里闪着兴趣,"我们正在组建临时医院,需要本地医生协助。
"冯·克莱斯特的马鞭突然指向陈志远:"这孩子会英语?
""家父曾在海关任职。
"齐修远不动声色地把孩子往身后挡了挡。
陈志远却探出头,用英语流利地说:"先生们需要茶还是咖啡?
"两个德国军官惊讶地对视一眼。
穆勒上尉蹲下身,从口袋里摸出块巧克力:"聪明的孩子。
你叫什么名字?
""陈志远。
"孩子接过巧克力却没吃,而是塞进袖袋,"意思是志向远大。
"德国人走后,医馆重归寂静。
齐修远翻开穆勒留下的德文医学手册,铜版纸上印着最新式的外科器械图样。
陈志远趴在一旁临字帖,毛笔尖在"仁心仁术"西个字上反复描画。
"先生,"孩子突然问,"德国人为什么杀我们的人,又要我们帮忙?
"毛笔在"术"字的最后一捺上洇开墨团。
齐修远望着窗外被炮火削去半边的槐树,想起海德堡医学院图书馆里那些安静读书的德国同学。
"人病了要吃药,"他慢慢说,"国家病了,就会发疯。
"未时二刻,张德海跌跌撞撞跑回来,脸色煞白:"先生!
菜市口...在杀头!
"齐修远正在研磨犀角,闻言石杵砸在臼里,溅起几点药末。
他抓起药箱就往外走,陈志远像条小尾巴似的紧跟在后。
长庆街比往日更萧条,几家店铺门板上贴着联军告示,墨迹未干的德文与中文并列:"窝藏拳匪者,格杀勿论。
"菜市口刑场围满了人。
齐修远挤到前排时,正看见刽子手举起鬼头刀——那是个穿着英军制服的印度兵,包头巾下渗出汗水。
跪着的犯人突然仰头喊了句什么,刀光闪过,头颅滚到齐修远脚边,眼睛还睁着,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。
"说是义和团余党。
"旁边卖炊饼的老汉低声道,"其实就是个掏粪的,捡了面红旗当抹布..."陈志远死死攥住齐修远的衣角,指甲隔着布料掐进肉里。
齐修远弯腰想捂住孩子的眼睛,却听见一声微弱的呻吟——刑场角落的排水沟里,躺着个血肉模糊的人影。
"还活着!
"齐修远冲过去,发现是个瘦小的中年人,右肩被子弹贯穿,腰间挂着个摔碎的砚台。
他迅速按压伤口止血,那人却挣扎着凑到他耳边:"南...南方...孙...""别说话。
"齐修远撕下衣摆包扎,血立刻浸透布料。
身后传来英军士兵的呵斥,他头也不回地用英语喊道:"这个人是我的药童!
"回医馆的路上,张德海背着伤者,不时左顾右盼。
陈志远小跑着跟在后面,怀里紧紧抱着齐修远的药箱。
转过观音寺胡同,突然闪出三个日本兵,明晃晃的刺刀横在路中央。
"站住!
"领头的军曹一把扯开伤者衣襟,"枪伤!
反抗军!
"齐修远深吸一口气,从袖中掏出冯·克莱斯特给的通行证。
日本军曹狐疑地翻看证件,突然用生硬的中文问:"你会接骨吗?
"原来日军驻地有个少尉坠马摔断了腿。
齐修远给伤者灌下麻沸散,在陈志远协助下完成接骨时,夕阳己经西斜。
日本军医送他们出来时,悄悄塞给齐修远一小包磺胺粉。
"南方..."担架上的神秘伤者当晚发起高烧,不停呓语着"起义""电报"之类的词。
齐修远用银针刺他人中穴,才发现他舌下藏着片薄如蝉翼的纸条,上面用蝇头小楷写着"八月十五,武昌"。
七月初八凌晨,伤者死了。
齐修远在整理遗物时,从对方鞋垫里找出张被血浸透的地图,上面标着几条奇怪的运输路线。
他把尸体埋在后院梨树下,陈志远蹲在一旁默默递工具,突然问:"先生,武昌在哪?
""长江边上。
"齐修远铲起一抔土,"很远。
""比海德堡还远吗?
"齐修远的手顿了顿。
十年前乘船离开汉堡港时,他以为那将是此生去过最远的地方。
如今站在满目疮痍的北京城里,却觉得欧洲近在咫尺,而武昌——那个从未去过的城市,反倒远得像在天边。
"先生看!
"陈志远突然指着天空。
一群信鸽掠过灰蒙蒙的晨雾,脚环在朝阳下闪着金光。
齐修远认出那是庆王府养的鸽子,往日这时候该往西飞,今天却齐齐转向东南。
七月初十,冯·克莱斯特带来个惊人消息:德军司令部批准齐修远重开医馆,专门救治联军中的热病患者。
德国人留下两箱药品和十袋面粉,还有本崭新的德汉词典。
"穆勒上尉很欣赏你。
"德国军官用马鞭轻敲靴筒,"下个月德皇特使来访,需要展示文明治理成果。
"齐修远抚摸着词典烫金的封面,想起海德堡旧书店里那个总给他留座的老店主。
"我需要通行证,"他说,"药材不够了。
""每天酉时前必须回来。
"冯·克莱斯特眯起眼睛,"听说昨天日本兵在你们后院挖出具尸体?
"陈志远正在擦拭显微镜,闻言手一抖,目镜滚到地上。
德国军官弯腰捡起来,突然用德语问:"孩子,你见过电报机吗?
""只在外滩海关见过一次。
"陈志远不假思索地用英语回答,又立刻改口德语,"是父亲带我去看的。
"冯·克莱斯特意味深长地看了齐修远一眼,临走时故意落下个牛皮公文包。
齐修远打开一看,里面是份标注着联军布防情况的地图,还有张照片——一队德国兵站在堆成小山的头颅前咧嘴笑着。
"收好。
"齐修远把地图塞给陈志远,"夹在《本草纲目》扉页里。
"七月十二,齐修远带着陈志远去城南搜罗药材。
被炮火轰塌的仁济堂药铺里,他们扒出半罐发霉的龙眼肉和几包虫蛀的当归。
回来的路上经过英国兵把守的粮仓,看见几十个百姓排队领救济粥,有个瘦成骨架的老妇人突然栽倒,再没起来。
"是霍乱。
"齐修远拦住要上前查看的陈志远,"去药铺后头找些苍术来,越多越好。
"当天夜里,齐修远熬了三大锅避瘟汤,让张德海分给街坊。
陈志远蹲在灶前添柴,小脸被火光映得通红。
他突然说:"先生,我想学把脉。
"齐修远搅动药汤的手停住了。
十年前父亲也是这样在瘟疫流行时连夜熬药,而他蹲在同一个位置,说出同样的话。
药气氤氲中,他仿佛看见父亲花白的辫子在蒸汽里晃动。
"手伸过来。
"齐修远擦干手,把孩子的三根手指按在自己腕上,"静心,数呼吸。
"陈志远屏息凝神的样子像个缩小版的郎中。
齐修远看着他睫毛在火光中投下的阴影,想起那个死在梨树下的陌生人。
武昌要发生什么?
那张地图又意味着什么?
七月十五中元节,本该烧纸祭祖的日子,京城却静得像座坟。
齐修远在后院摆了张矮几,供上三个馒头——给父亲,给死在刑场的无名氏,也给陈志远从未谋面的父母。
陈志远学着他的样子焚香叩拜,突然问:"人死了真的会变成鬼吗?
""会变成星星。
"齐修远指着刚亮起的天狼星,"你爹娘就在那看着你。
"孩子仰头望着星空,眼泪无声地流到腮边。
齐修远轻轻揽住他单薄的肩膀,感觉掌心下的骨头硌得生疼。
夜风掠过梨树,那片新翻的土己经长出嫩草。
七月十八,穆勒上尉突然造访,带来个发着高烧的法国军官。
齐修远诊脉后发现是伤寒,用白虎汤加减治疗。
德国军医全程观摩,对齐修远在病人脚底敷吴茱萸的手法大为惊叹。
"太神奇了!
"穆勒捧着笔记本狂记,"这比我们用的冰敷法有效多了!
"齐修远正在写药方,闻言笔尖一顿。
他想起海德堡教授说过的话:"医学不该有东西之分,只有有效与无效之别。
"陈志远机灵地递上刚烘干的药碾,里头是捣好的羚羊角粉。
"先生,"送走德国人后,陈志远小声问,"洋人为什么总说我们落后,又要学我们的医术?
"齐修远正在擦拭被法国人弄脏的诊榻,闻言首起腰来。
透过支摘窗,可以看见德国兵在对面屋顶架设电报天线,细长的金属线在夕阳下闪着冷光。
"知道针灸为什么能止痛吗?
"他反问道。
陈志远摇摇头。
"因为人体自有经络,与种族无关。
"齐修远指着院里的梨树,"就像这棵树,德国人叫它birne,英国人叫pear,可结的果子都一样甜。
"七月二十,冯·克莱斯特突然派兵"请"齐修远去给日本领事看病。
回来时己是深夜,陈志远还守在灯下抄《汤头歌诀》,见他进门立刻端来热在灶上的杂粮饭。
"日本领事得了怪病,浑身起红疹。
"齐修远疲惫地坐下,从袖中摸出个小纸包,"这是他们军医用的消炎片,收好。
"陈志远好奇地拆开纸包,里面是两片白色药片和一张字条。
他展开一看,上面用德文写着:"八月一日,待在医馆。
""先生..."孩子刚开口,就被齐修远制止。
院墙外传来巡逻兵的皮靴声,由近及远,最终消失在夜色中。
"明天开始,"齐修远吹灭油灯,在黑暗中小声说,"我教你认德文字母。
"七月二十二,酷暑难当。
齐修远带着陈志远去什刹海采芦苇根,看见湖面漂着几具肿胀的尸体,有野狗在岸边啃食。
他们绕道西西牌楼,发现贴满联军告示的墙下多了张新布告——朝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,即将与联军议和。
"先生,议和是什么意思?
"陈志远踮脚看着布告。
"就是..."齐修远突然哽住。
十年前他离开德国时,柏林报纸上登着胶州湾事件的照片,标题是《德国在亚洲的又一胜利》。
如今站在残破的牌楼下,他忽然明白了一个残酷的事实:弱国的书生,连解释"议和"二字的资格都没有。
回家路上经过英国兵营,听见里面传出留声机的音乐声。
陈志远扒着门缝偷看,被齐修远拽回来时小声说:"他们在跳舞...还有个穿红裙子的中国女人..."齐修远捂住孩子的嘴快步离开。
转过两条胡同,迎面撞见张德海慌慌张张跑来:"先生!
快回去!
德国兵把医馆围了!
"医馆门口站着六个持枪德军,冯·克莱斯特正在翻检药柜。
见齐修远回来,他啪地合上手中的《瘟疫论》:"有人举报你藏匿革命党。
""这里只有医生和病人。
"齐修远平静地说,感觉陈志远的手在他掌心发抖。
德国军官冷笑一声,突然用马鞭挑起地窖盖:"是吗?
那下面是什么?
"地窖里躺着三个霍乱患者,都是附近街坊。
齐修远刚要解释,穆勒上尉匆匆赶来,在冯·克莱斯特耳边低语几句。
德国军官脸色变了又变,最终只是狠狠踢翻了药碾。
"明天起,所有病人必须登记。
"他甩下一叠表格,"包括死亡证明。
"当晚,齐修远在灯下研究那张神秘字条。
陈志远己经熟睡,手里还攥着德语单词本。
窗外月光如水,照得梨树下那片新草格外青翠。
远处隐约有马蹄声,像是从东交民巷方向传来的。
七月二十五,暴雨。
齐修远正在教陈志远配药,大门突然被撞开。
一个浑身湿透的清军军官跌进来,右胸插着半截箭矢。
张德海刚要关门,街口传来日本兵的哨声。
"求您..."军官咳着血沫,"把...这个...交给..."他塞给齐修远个油纸包,就断了气。
暴雨掩盖了血迹。
齐修远把尸体藏进地窖,打开油纸包——里面是把精致的左轮手枪,枪柄上刻着"楚"字。
陈志远瞪大眼睛,小手不自觉地摸向枪管。
"去烧锅开水。
"齐修远迅速包好枪,塞进灶台暗格,"再把《伤寒论》拿来。
"雨声渐歇时,日本兵来搜查"逃兵"。
齐修远用流利的日语解释死者是霍乱患者,还故意让他们看溃烂的伤口。
军曹捂着鼻子退出去,在门槛上绊了个趔趄。
七月二十八,齐修远被紧急召去德国公使馆。
回来时带了个沉重的皮箱,里面装满医学书籍和手术器械。
陈志远发现先生的白布袜上沾着血迹,袖口也少了一颗盘扣。
"公使夫人难产。
"齐修远轻描淡写地说,从怀里摸出个苹果给孩子,"穆勒上尉送你的。
"陈志远啃着苹果看齐修远整理书籍,突然指着本德文书惊呼:"先生!
这上面有枪!
"那是一本《战地急救手册》,扉页照片里排列着各式武器。
齐修远快速翻到某页,指着一行德文念道:"止血带使用不宜超过两小时——这才是重点。
"夜深人静时,齐修远悄悄取出油纸包。
手枪在月光下泛着蓝光,枪膛里还有三发子弹。
他想起白天在公使馆听见的只言片语——俄国人增兵东北,德国准备强租胶州湾,而南方某个港口城市,似乎爆发了起义。
七月三十,陈志远第一次完整写下自己名字。
毛笔在宣纸上划出稚拙的笔画,最后一捺却力透纸背。
齐修远看着这个从废墟里捡来的孩子,忽然想起《庄子》里的话:"泉涸,鱼相与处于陆,相呴以湿,相濡以沫...""先生,"孩子举着字纸,眼睛亮晶晶的,"我写得对吗?
"齐修远摸摸他刚长出发茬的头顶:"很好。
明天教你写天下为公。
"窗外,暮色中的北京城炊烟袅袅。
不知谁家在烧艾草,苦涩的烟味飘进医馆,与药香混在一起。
更远处,联军军营的探照灯划破夜空,像柄雪亮的长剑,刺向东南方的星辰。
同类推荐
 全家都爱养女,我被顶级大佬夜夜亲红温(谢书瑶谢书雅)热门小说排行_完结版小说全家都爱养女,我被顶级大佬夜夜亲红温谢书瑶谢书雅
全家都爱养女,我被顶级大佬夜夜亲红温(谢书瑶谢书雅)热门小说排行_完结版小说全家都爱养女,我被顶级大佬夜夜亲红温谢书瑶谢书雅
晨曦
 女皇她不想上朝(沈君泽谢九仪)最新好看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女皇她不想上朝(沈君泽谢九仪)
女皇她不想上朝(沈君泽谢九仪)最新好看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女皇她不想上朝(沈君泽谢九仪)
一元两块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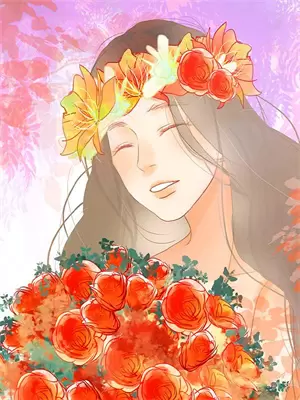 重生后我势要考大学何倩徐晴免费小说全集_免费阅读无弹窗重生后我势要考大学何倩徐晴
重生后我势要考大学何倩徐晴免费小说全集_免费阅读无弹窗重生后我势要考大学何倩徐晴
柚紫汁
 恶毒男配和路人甲在一起了(苏昊焱莫席琛)最新章节列表
恶毒男配和路人甲在一起了(苏昊焱莫席琛)最新章节列表
柚紫汁
 我帮助的舍友背刺我(曹景辉魏雨)完整版免费全文阅读_最热门小说我帮助的舍友背刺我曹景辉魏雨
我帮助的舍友背刺我(曹景辉魏雨)完整版免费全文阅读_最热门小说我帮助的舍友背刺我曹景辉魏雨
柚紫汁
 教便衣摊煎饼教出个女朋友(抖音热门)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教便衣摊煎饼教出个女朋友全文阅读
教便衣摊煎饼教出个女朋友(抖音热门)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教便衣摊煎饼教出个女朋友全文阅读
柚紫汁
 丈夫为了帮洛丽塔出气,把我的私照做成剧本杀插图裴砚霆楚楒瑶热门的网络小说_完整版小说丈夫为了帮洛丽塔出气,把我的私照做成剧本杀插图(裴砚霆楚楒瑶)
丈夫为了帮洛丽塔出气,把我的私照做成剧本杀插图裴砚霆楚楒瑶热门的网络小说_完整版小说丈夫为了帮洛丽塔出气,把我的私照做成剧本杀插图(裴砚霆楚楒瑶)
一只小懒猫
 五一当天,读者留言要晚八点吊死我(抖音热门)无弹窗小说免费阅读_小说免费阅读无弹窗五一当天,读者留言要晚八点吊死我抖音热门
五一当天,读者留言要晚八点吊死我(抖音热门)无弹窗小说免费阅读_小说免费阅读无弹窗五一当天,读者留言要晚八点吊死我抖音热门
空鹿
 此妈非彼妈(刘慧小玲)小说免费在线阅读_此妈非彼妈(刘慧小玲)大结局阅读
此妈非彼妈(刘慧小玲)小说免费在线阅读_此妈非彼妈(刘慧小玲)大结局阅读
青夏
 天价招婿(张明望薇薇)在哪看免费小说_已完结小说推荐天价招婿张明望薇薇
天价招婿(张明望薇薇)在哪看免费小说_已完结小说推荐天价招婿张明望薇薇
姚期







